音樂,是我可以做得比別人更好的事
總被冠上搖滾女王稱號、也得過金曲獎,楊乃文很早就發現唱歌這件事對她來說駕輕就熟。從小學開始,總是可以在音樂課拿下高分,求學路上,舉凡唱詩班、歌舞劇等和音樂有關的活動,總是抱持「先加入再說!」的想法,全心投入。
有一種論述是,當某個人在某個領域中得到成功,人們會將他過去的相關經歷編織成串,倒果為因地推論這是該人立志得早、因此在長期耕耘下如願邁向成功;甚至更偏激地認為應該屏除路途中其他的分歧或雜音。
具體而言可能會是下面這種常見的質疑:如果念了數學系,為什麼要去玩樂團?如果要賣雞排,又何必念博士?對楊乃文來說,音樂的確是她所擅長的事,也很早就決定走上唱歌這條路。「如果唱歌這條路走得不順、去做了別的事,對我來說那才是轉彎。」小學時舉家移民到澳洲,楊乃文因為對唱歌的熱愛,決定在大一結束後休學一年,返台尋找機會。那段時間中,她在 pub、livehouse 等表演空間中結識了李雨寰、林暐哲等知名音樂人,爾後於 1997 年發行首張個人專輯《One》。
唱歌是楊乃文的興趣,也是志業。這兩者的差別有何不同?「我覺得『作夢』跟『去實現一個夢想』是兩件事。很多人喜歡作夢,但有些人真的會踏出第一步,把夢想變成真實的東西。」進一步言,如果你有好多的興趣,該怎麼踏出那第一步?往哪裡踏?楊乃文說,「我喜歡做我覺得我很厲害的事情。」知道自己的興趣、並成為該領域中的佼佼者,是她之所以將音樂視為志業的原因之一。
「生物跟遺傳學是我有興趣的事情,但我知道我不是箇中翹楚。不過,我完全不會否定另外一種想法,就是當我對這個行業很有興趣時,即使不是頂尖,也可以做得很開心。只是這對我來說,不會是(志業的)首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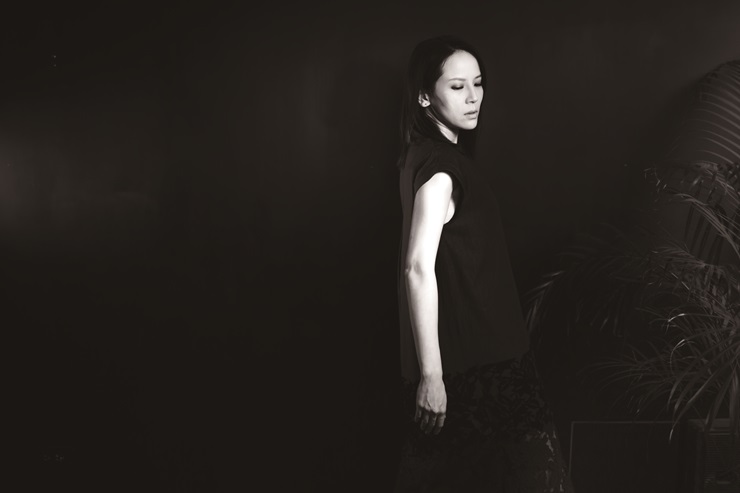
有知識可以吸收 why not?
較少為人知的是,楊乃文大學時主修的是生物與遺傳學。看似與音樂之路完全不相干,在倡導學用合一、無縫接軌的現代價值觀中,顯得特別。「吸收知識」在台灣常帶有強烈的目的性,如得到好學歷、好工作等。但楊乃文認為,知識的美好不在於其利用價值,而是用來理解世界。
「我不是那種覺得一定要或一定不要唸大學的人,也不覺得大學唸的東西一定要跟你後來做的事情有關。」她的提問是,有知識可以吸收,有什麼不好?學習的項目若跟未來職業沒有直接相關,難道就不用學了嗎?她認為,「學」與「用」不必然需要緊緊連結,也不應該因為決定了未來的方向就自我限縮吸收知識的維度。
「我不會因為我念生物學就不唱歌、也不會因為我唱歌就不去吸收其他知識、或因為和工作沒有直接相關,就覺得去學別的東西是種浪費。你不應該因為已經選了一件最想做的事情,就覺得人生只有這個。」
371.jpg)
高中、大學是大多數學生開始探索並找尋興趣的時期,在澳洲就學的楊乃文,分享當地高中的一項傳統:在澳洲,高一生可以選擇一至二個機構進行為期兩週的實習,當時,她選擇了建築與會計事務所做為實習目標。能夠有機會到自己從未接觸過的領域實習,對還是高中生的她來說是難得的體驗,而在這之中,雖然不用揹負一般正職員工的壓力,卻也能對行業的面貌略窺一二。
「我當時的自我認知是,建築沒天分、會計超級討厭!」楊乃文認為,有些人是從小就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想做什麼,並且能一路堅持下去。但對她來說,世界上從來就是有好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要怎麼知道自己適合哪一種?是不是只是三分鐘(甚至三秒鐘)熱度?
實際嘗試就顯得很重要。不去試,自然就對陌生的事物缺乏認識,但要能踏出第一步,前提是心態要夠開放。楊乃文說,人總是本能地傾向去從事自己本就擅長、或有興趣的事,但所謂的熱情其實沒那麼容易找到。
「這不是一件令人灰心的事情,反而是你如果對很多事情都沒興趣的話,應該去接觸更多事物。」否則自我封閉,更不會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了。「你問為什麼要學遺傳學。為什麼不要遺傳學?它超有趣的!」
心態開放之必須
言談之中會發現,楊乃文其實很清楚自己擅長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人不要不自量力,『認識自己』非常重要。」唱歌無庸置疑是她所能做、而且做到頂尖的事,但一路走來,她也透過生命經驗,了解自己的侷限。比如哭戲。
剛出道時,楊乃文拍過 MV,也有不少劇本找上門。「拍哭戲,擠眼藥水擠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有一滴很漂亮的眼淚。如果有劇本是要我一直痛哭,那真的沒辦法。」很有趣的經驗是,曾有劇本邀約她飾演一個能歌善舞的同性戀機器人,楊乃文說,「如果我是演員,應該會很想挑戰這個角色吧!」但在認識到自己能力範圍的情況下,也就不會盲目向前衝,而能往其他更有辦法發揮的領域前進。
然而,認識自己的同時,也必須理解他人。單看楊乃文的外表與風格,可能會認為她是對條條框框有所堅持的人,但理解與對話,對她而言比堅持自己更至關重大。
「我覺得開放的心態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她不認為世界上有絕對的好壞、美醜、是非,價值碰撞也不盡然平靜無波,端看「你有沒有辦法接受他們同時存在。」聽到一句話、看到一禎藝術作品,有時候你完全不認同那樣的呈現,但對楊乃文來說,背後代表創作者有著跟她完全不一樣的審美觀與想法。

從執著到轉念的定、靜、安、慮、得
在這幾年的歌唱之路中,曾有過想放棄的念頭嗎?楊乃文幾乎是反射性地回答,「每天!」
「在任何領域裡你一旦投入,就會計較著付出與犧牲足不足夠交代你在這份工作中的位置,但久了之後我會提醒自己不要這樣想,不然還蠻傷害自己的。其實事物大多時候都不是平衡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 2+2=4,所以你要打開心胸,幫助自己找到平衡。不是去深究那些已經錯失的,而是轉念,去做其他你可以做的事。」
牛角尖上的日子過久了,漸漸也就學會放過自己。身上銳利的刺也許會隨著時間改變想法而消失,但楊乃文後來發現,現實中被一點一點消磨掉的那些角,會在他處繼續開展出新的姿態。演藝工作是個必須不斷像太陽般燃燒自己、給出能量的型態,她說,如果可以的話,希望能夠停下來。不是不斷的說,而是有更多時間好好地諦聽這個世界。
都說創作反映自身,也共振著聽者心上正好緊繃的弦。從〈一個人〉、〈星星堆滿天〉、〈Silence〉,鼓點漸歇來到〈漂著〉、〈我離開我自己〉、〈未接來電〉,那些熱烈的低迴的嗓音,帶你進行一場又一場時空旅行。音響中傳來過去的楊乃文,被聲音攫住的你,聽著她,帶著她聲音的銘刻,更迭到下一個未來。路上,你偶爾錯失了什麼、迷失了航向,楊乃文說,如果已經不知道要走向哪裡,先停下來想想。
一轉念、一旋身,此刻或許又是適合出發的好時候。
328.jpg)
BACK TO LIVE. BACK TO MUSIC.
「其實事物大多時候都不是平衡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 2+2=4,所以你要打開心胸,幫助自己找到平衡。」之於音樂,之於信仰,之於我們共同編織的「極致又純粹的搖滾時代」。
『TIMEQUAKE』一詞源於科幻小說家馮內果的文學著作,意指時間發生大地震,過去現在未來,次序錯位,逆行重複,既存的宇宙迸發了新的虛實意義。而這個反叛現實的大膽假設,被巧妙地運用在此次演唱會裡,成為重要的精髓梗概。突破框架玩味新意,重現音樂的真實本質,貫穿於『原味經典』與『實驗創新』之間,徹底展現楊乃文獨特的音樂魅力與無法取代的現場表演風格。
『TIMEQUAKE』演唱會不以華服取勝,少了特效煙硝味,以音樂文本,精新佈局的編曲與樂器編制,層次有致高潮迭起的音樂呈現,揉和著我們熟悉的楊乃文,也有我們驚豔的楊乃文,游移在獨立與主流的混沌時代,一場飄揚在過去、現在、未來錯置的 TIMEQUAKE 演唱會,讓我們在燈光亮起時,都回到記憶中的美好舞台。
一場 TIMEQUAKE,時間的大地震,讓所有人的美好時刻因此相互震盪與重置,回到那個「極致又純粹的搖滾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