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 如影隨形
動物,乍聽這個名詞,感覺既熟悉又陌生,你可能想起身邊親近的阿狗阿貓、遙遠撒哈拉沙漠的駱駝,或者是動物園裡的長頸鹿,當然身為靈長目人科人屬的人類也是動物界的一員。動物在生物的定義上大都為多細胞真核生物,並且以攝食其他生命體(植物或其他生物)維生,所以為了果腹、生存,獵食行為絕對少不了,在人類的角度看來可能覺得相當血腥、不忍直視,但在生物界弱肉強食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本能。
在《大動物園》成書之前,何曼莊的文章在 OKAPI 讀書網站以專欄的型式連載(恰巧 OKAPI 也是動物的名字,名為「狓」),書寫的過程中,並沒有什麼夢幻、可愛的心情,反倒時常要面臨血腥和殘酷。「其實很多人長大後也知道動物園是很殘酷的,在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書中談到人類看到他人受苦時會不想看且避開,也探討此行為究竟是不忍或是麻木。而面對殘酷就是我的工作,寫《大動物園》就得講這些事、面對與它共存的事實。當然我們的目的是去減少它,但首先要承認它的存在,很多人類生活中也充滿殘酷,只是不願意去想罷了。」何曼莊說。
人類開始對動物有感情進而吃素,這是文明的結果、是一種高度智能的發展,因為違反生物本能。「如果大家是藉動物來練習情感表達的話,當我們對動物產生感情、有同理心時,希望也能將這份感受好好轉化成對待身邊的人。」

我是最不願意一開頭就提到死亡的。
死亡、或是諸如此類的話題,總會讓人想要別過頭去或是閉上眼睛,因為那些畫面對於愛護生命的心靈來說太過醜陋,但遠方一隻長頸鹿的死提醒我,所有對生命的愛護都應該包括面對死亡。
2014 年 2 月 7 日,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動物園裡,飼養員使用電擊槍,乾淨俐落地殺死了一隻長頸鹿,他們說這樣做能將死者的痛苦減到最低,且不會使動物遺體內有毒物殘留,是大部分先進的電動屠宰場採納的方式。
⋯⋯
我認為不讓孩子認識死亡不是好事,問題在於地點─動物園不是屠宰場,即便宰殺的過程百分之百符合歐盟規約,「在動物園殺死健康動物」這件事情不應該合理化,當「基因過剩」成為殺戮的正當理由,動物園原本就很脆弱的立足點也就開始動搖、嚴重地動搖。─節錄自《大動物園》〈第二隻長頸鹿〉

書寫大動物園
「OKAPI 專欄主要是希望介紹、分享書籍給讀者認識,當時的我人在大陸,在很多書都沒有的情況下去北京圖書館瘋狂地搬出一疊一疊的書翻閱,時間壓力下快速地吸收、速讀,連旁邊的高中生都忍不住睜大眼、震驚地看著我。」
除了透過實際去動物園觀察,何曼莊更大量地翻閱書籍,讓專欄不似遊記,文中融入大量歷史、人文、藝術、自然、音樂等,彷彿小型百科全書,時而一針見血批判、時而帶著浪漫的步調、時而諷刺又帶點俏皮的方式,令人看得相當過癮。她用清澈的雙眼洞悉這個世界,赤裸的,像是被扒了皮的狐狸,少了毛絨絨的虛偽。
創作講求方法且不容許自己延遲交稿的何曼莊,在時間滴答滴答流逝時不斷地鞭策自己,「當作家最大的危機就是會精神崩潰,我常跟朋友說做藝術、創作就像走鋼索,會走的人才會走,走習慣就跟平常走路沒什麼兩樣,但不能否認是一旦摔下來,就會死掉。」何曼莊貼切地形容在創作路上,排山倒海崩潰、混亂的過程,除了這條路很孤獨外,經常要面對自我懷疑和他人的懷疑。

時光拼湊成的剪影
在《大動物園》完成前最大的挑戰就是要把原本一篇篇專欄文章串起來變成一本書,並且下一個結論。何曼莊認為,書的產生是要傳達某種訊息,單篇連載文章和成書的文章顧及面向是不同的。連載時可能會想這星期該講什麼主題、要埋怎麼樣的梗逗讀者;書會複雜許多,每個章節的編排順序,以及想傳達什麼,或是藉由文章的刪減達到想要的呈現方式,不可置否的,這些都要考慮進去。

她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整理、統整並串連起來,「把倫敦動物園擺在第一章,是因為這是國外第一個逛的動物園、是歐洲動物園之旅的起點;最後一章則是特意放台北動物園,有種回家的感覺,也是幼時回憶。」
《大動物園》把場景由外拉到內,回到自己最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何曼莊表示《大動物園》的結論在經歷這整本書的過程、人生淬鍊中慢慢浮現,正如同她跟聶永真說,封面設計除了要有動物外,希望「人」佔很大的篇幅,對她來說沒有人類的愛是不可能完成這件事,因此在書的最後一一感謝那些曾經幫助她的人,不管是在旅程上提供住宿、開車帶她去動物園、相隨在動物園路上的好朋友及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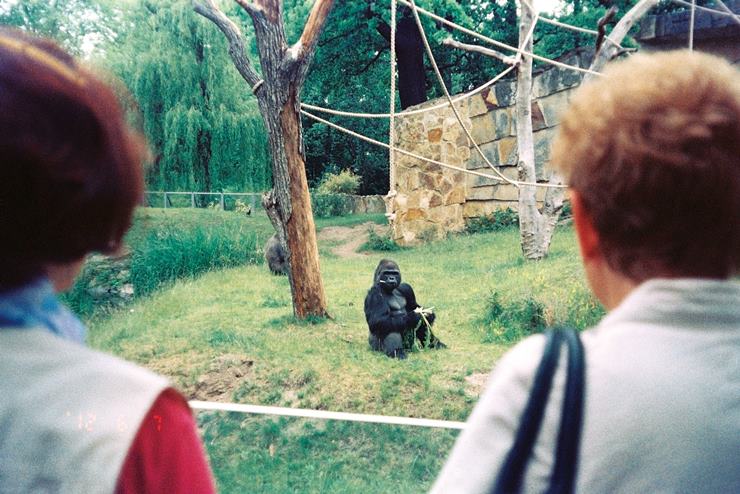
動物園是一座記憶載體,把美好的回憶牢牢地抓在地上。當你看見面前一座動物園,它其實不只是一座動物園,它是一個城市的記憶,保存著曾經在這裡活著的人與動物的大小回憶。除了地震、火災、海嘯、暴動和恐怖攻擊,一座城市也可以擁有玫瑰色的、糖果氣味的、或者動物嘰嘰叫佐以遊行鼓號樂的集體記憶。─節錄自《大動物園》〈台北動物園:一座城市的回憶〉

動物園的各種樣貌
西方的動物園發展較悠久,不管是制度上或是軟硬體設施上考量較周延,大家都很習慣公共設施的存在,而將場域拉到中國時就會成為另一種風景。「印象最深是文化差距跟生活體驗,兩邊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要學著適應跟抽離。在中國,他們很習慣保密,且能不惹麻煩就不會多管閒事。像是有次去哈爾濱北方森林動物園請開遊園車的大姐載我去大象館,想不到她帶我去看河馬,並且說大象生病了。後來又問了一個人,卻又說大象出差去了⋯⋯。」
動物園的存在本身就充滿了矛盾。自然環境被人類破壞後,很多物種快速消失,野外的物種都在滅絕的邊緣,動物園彷彿諾亞方舟般,保存了某一小部分的動物及基因,這樣的意義是如何?而只能存在人工生長環境的動物,一旦放生後會招受更大的威脅,永遠也回不去原本的狀態,何曼莊說:「動物園存在的價值似乎只剩保育跟教育意義。」

從生命中掙扎 破繭
「每個人年輕時都會有年輕時的困惑,因為是必經之路,到另一個階段又會遇到某個階段混亂的過程。」何曼莊認為創作和旅行都可以反映人生階段,在二十歲左右、剛出社會時,不確定人生方向,很多人一定也常遇到當別人問近況時不是支支吾吾就是不想回答的情形,也因為缺乏信心、心情起伏較大,二十歲到三十歲的這十年,心情是最忐忑、迷惘的。
尤其身為藝文工作者更時常面對餓不死、但不知道下一筆資金什麼時候會進來的憂患意識,向外尋求資源也是種方法。何曼莊不時會寫計畫投給私人或機構尋求贊助,曾經也被拒絕、駁回計畫,因此在做《大動物園》時先自掏腰包、同時進行OKAPI 專欄,「他們其實不相信我能做到那些事,所以等做到一半進度、有些成績了才去申請,證明我辦得到⋯⋯,慢慢累積信用後,現在還沒動筆寫時就可以申請新的計畫。」
當然,比起台灣,歐美各國對藝術、創作等領域是較受重視且保護的。當一個外國人在歐洲找工作時需要工作簽證,如果你是歐盟的公民,從事藝文創作是相當有保障的,而一旦是非歐洲公民的話,不好意思,好處會通通收回,因此何曼莊最後決定待在美國。美國本來就是由移民組成的國家,工作簽證也分成好幾種,相較於歐洲,美國對於別的國家的人能更包容,且可以自由地、無後顧之憂地創作。

一個古老的動物園總是不卑不亢地乘載時代流轉,比任何朝生暮死的樓房更加誠懇反映了城市的性格,那些安穩已久的歐洲動物園看似有一種塵埃落定的優雅,對比起來,中國此刻的動物園百態,證明了這是一個充滿不安的時代。──節錄自《大動物園》〈北京動物園:中國最硬的鐵板〉

蛻變
旅行的優點是擁有新鮮感,看到一切新奇的人事物,總是帶來驚喜、愉悅、新發現,但是當旅行過這麼多地方後,似乎很難像當初一樣容易掀起漣漪,甚至在過度頻繁移動時,何曼莊只要想到幾個月後就會離開某個地方,便沒辦法花精神、力氣去建立與土地的關係或聯結。「旅行和旅居不太一樣,在心裡也分得很清楚,現在我回到曾生活多年、熟悉的紐約市,感到自在且習慣,所以台灣是我的家,紐約也是我另一個家。」曾經,何曼莊缺乏與自身居住城市的歸屬感,搬家也無法改變那種狀態。
現在,旅程結束後,何曼莊不想再到處飄泊,而想在某個地方久待,希望比較「負責地」和地方建立起關係。
何曼莊在《大動物園》書寫的過程中,穿梭在各地方的動物園,在這條路上不斷地自我辯證、不時拋出疑問,而讀者也能隨著她探索的歷程、片段殘影中拼湊自己相關的部分,藉著閱讀作者的成長、蛻變,希冀自己追求更好的狀態活著。

其實沒有甚麼遠大動機,起初走進動物園只是想要逃避人類,在路上的兩年,有時喝酒、有時跳舞、有愉快自滿的日子、也有寂寞崩潰的時刻,無論如何,這趟旅途,沒有某些人類的支持與愛護無法完成,謝謝⋯⋯。──節錄自《大動物園》〈給某些人類的感謝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