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的文化衝擊
第一次到阿語系國家,奇慈飛正值大三,就讀政治大學阿拉伯語系的她,意外選擇了北非突尼西亞做為大三交換學生的國家。先撇開到突尼西亞留學這件事不談,光是選擇阿拉伯語系作為大學主修就已經夠特別了!當我們問到這個問題時,奇慈飛表示,當時她單純覺得阿拉伯語系很酷,而且像是英文、日文這類熱門的語言都已經有很多人專攻,不如選擇一個較為特別的語言學習,而且自小就對語言充滿興趣與自信的她,當時信心滿滿的認為一定能駕馭這個神祕的語言。
但,等到真正接觸阿拉伯語言後,才知道自己所學的不足。恰好在阿語系有個不成文傳統,大三時會到阿拉伯語系國家留學,體驗當地文化,也讓自己沉浸於那樣的環境中,增強語言能力。可是到了突尼西亞,一切都不如奇慈飛所幻想的模樣。


「旅遊與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兩碼子事,當你對一個文化不夠熟悉時,想要融入當地就變得非常困難。」甫到突尼西亞,奇慈飛被那地中海風情的悠閒氛圍及異國情調深深吸引,但沒過多久,這樣的好心情立刻被承辦居留業務的警察打破。因為申請居留證的需求,奇慈飛到警察局詢問該如何辦理,承辦的警察要她到另一間警察局去,沒想到到了另一間警察局,那邊的警察又要她到別間去,就這樣顛沛流離了數家警察局後,又回到最一開始的警察局,也確定了是由該警察局負責。
好不容易填寫完表格,詢問對方何時會通過,對方只笑笑的答了一句「Inshallah(註),下星期吧」,讓奇慈飛相當困惑,等到下星期到警察局取件時,對方卻說還沒辦好,此時的她已經抑制不住怒火,當場質問對方為何沒有遵守上週的承諾?此時,警察只是笑笑地從抽屜拿出奇慈飛的居留證遞交給她。
面對這樣的舉動,剛到突尼西亞的奇慈飛相當不能接受,但在當地居住一段時間後,她也逐漸能理解為何那位警察會如此漫不經心,因為,那可是地中海國家啊!誰會在地中海匆匆忙忙、庸庸碌碌的過日子?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氛圍,讓所有人的生活步調變得緩慢,處理事情也不急不徐,還喜歡開點小玩笑,只是這麼樂天及悠活的民族性格,實在讓她很難適應。

異中求同
在突尼西亞求學時,奇慈飛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男人注視女人的眼神。她舉例,有一條街上全都是咖啡店,許多年輕人或無業人士就在咖啡館待上一整天,抽水煙,看球賽,除此之外,還有欣賞路上正妹。
或許當地女性早已習慣這樣的「景色」,但奇慈飛完全無法適應,因為當有女生行經那條街時,咖啡館裡的男性們就會投以打量眼光,而且一次就是數百隻眼同時投射過來。雖然以一個外地人的角度,會覺得很不可置信,但這對當地人而言,似乎已經是一種日常風景。有時或許是外人的大驚小怪,但文化差異就是如此吧,身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台灣小妹妹,很難立刻習慣這樣的差異性。

這樣的現象並非舉國皆是,奇慈飛也有很要好的當地男性友人,而後來到了約旦,也發現不同國家對於女性權利的重視更是不同。「在突尼西亞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所謂的『女性地位』在阿拉伯國家與在台灣非常不同。但其實許多阿拉伯國家都在提倡女權運動,埃及、摩洛哥也有許多電影以女性為主題,政府對於女權的主張更是不遺餘力。」
奇慈飛在大學畢業後,又到了約旦就讀語言學校。對於約旦,她也有說不完的故事。約旦算是阿拉伯語系國家中相當先進的,在這個國家,你可以看到許多新潮的展覽、文青咖啡館、街頭藝術表演等等,與一般人所想像的中東世界有極大落差。而在約旦求學時,奇慈飛也發現到約旦校園與台灣校園的相異之處。
走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隨處可見青春洋溢的大學生成群練舞、玩遊戲、彈吉他等,也不時有社團舉辦活動,諸如擺攤義賣、社團成果表演等等,替大學生活增添許多樂趣。可是在約旦大學校園中似乎不見如此現象,奇慈飛說明:「對約旦的大學生而言,校園就是個學習的地方,或許因為我是就讀語言學校,並未參與一般課程,但就在我求學時,並未看到像台灣校園這麼活潑的社團活動,不過也是有一些慶典,像是韓國日、中國日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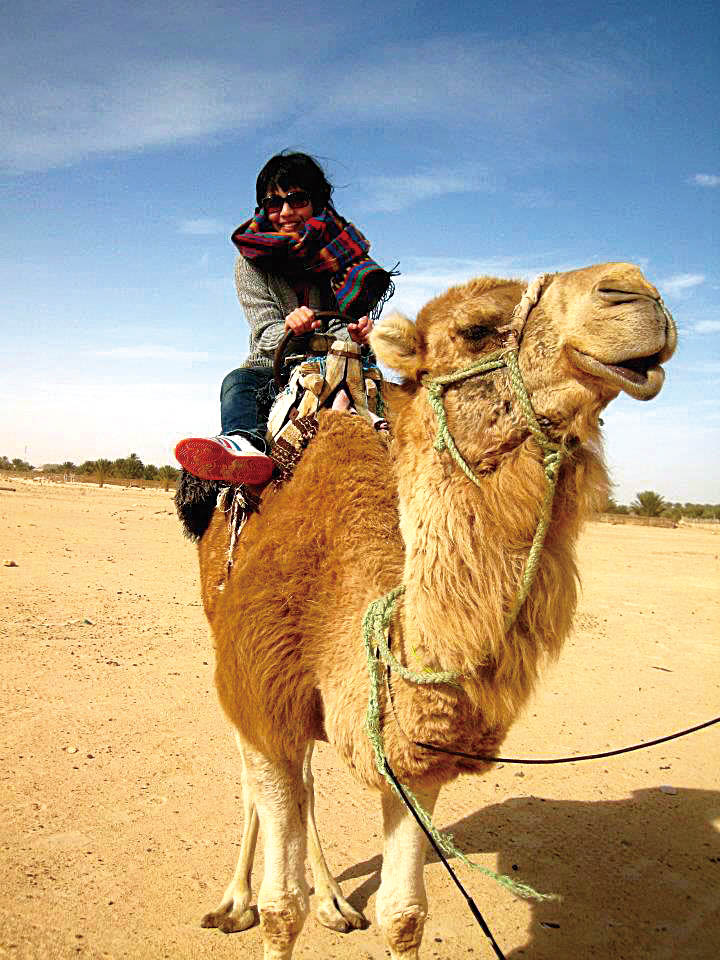

異鄉之情「催淚」流
若說起在阿拉伯語系國家求學所發生的精彩小故事,非催淚瓦斯事件莫屬了。奇慈飛到突尼西亞交換學生時正值茉莉花革命後沒幾個月,當時家人都很擔心,但她自己卻一派輕鬆,並沒有太多懼怕。
到達突尼西亞後,發現其實當地還算滿平和的,沒有看到所謂的暴動或抗爭,但就在某天早晨,奇慈飛與友人步出宿舍後,發現街上滿是抗議民眾,而且空氣中飄著白色的煙,讓人幾近窒息,眼淚狂流,原來是當地警方丟出催淚瓦斯驅趕民眾。奇慈飛與友人見狀立刻狂奔回宿舍,但正當要把宿舍大門關上時,有個當地民眾為了躲避催淚瓦斯的攻擊企圖跟著進入宿舍,礙於宿舍規定,奇慈飛與友人只得請那人離開,而她們也看著那人逃進滿是濃煙的大街上,心中百感交集。
說起這段經歷,奇慈飛依然感到心驚膽跳,眼睛還可以感受到當時的刺痛感,而心中對於那個被她們趕出宿舍的陌生人,更是有說不上來的情緒,「雖然那次事件真的很可怕,但幸好沒有釀成什麼傷亡,而且因為當地人的樂天性格,過幾天又立刻回復到正常生活了」。


馬不停蹄的遊走天涯
澳洲打工正夯,奇慈飛現在人也在澳洲,但她選擇的是另一條路,這條路比較不易找到,因為總共只有五個國家的五位年輕人可以走上這條路,這是由澳洲政府舉辦的 The Ultimate Gap Year Queensland 計畫,針對 18 到 30 歲的年輕人,提供他們在澳洲實習工作的機會。奇慈飛擔任的工作是行銷助理,雖然不是她的專長,但正在努力學習中。談到現在的生活,奇慈飛不諱言的說,澳洲的生活不如她所想的美好,雖然觀光景點很多,城市也很繁榮,比起阿拉伯,這邊的生活舒適多了,但不知為何,心中老是想著突尼西亞還有約旦,懷念那些超級熱情的阿拉伯人。
「所謂的文化沒有優劣之分,對我而言無論是阿拉伯或是澳洲,都有非常棒的歷史及文化,只是,阿拉伯世界給我了『家』的感覺,讓我感受到歸屬感,而在澳洲,我卻像個過客,甚至可說是有點迷惘了。」奇慈飛在與我們訪談最後這樣說道。

「如果要讓眼界大開,再近的國家都能替你辦到;但如果自己沒有打開心靈,就算到了世界的盡頭,依舊覺得乏味。」在阿拉伯世界所待的兩年,給了奇慈飛截然不同的全新角度看世界。
以往,總是習慣以西方文化檢視這些從未踏足的國家,但當踏上突尼西亞及約旦兩個國家的國土後,奇慈飛才意識到從前的自己眼界有多麼狹隘,而這視角轉變的過程也讓她重生了。待在阿拉伯國家,自己變成了他人檢視的對象,雖然偶爾還是忍不住以自身角度批判當地文化,但該文化對自己的反饋又立刻讓自己重新反省。人活著就是要勇於做自己不敢做的事,如果少了這些挑戰,生活該有多無趣啊!

一個讓外國人摸不清意思的詞彙─ Inshallah
Inshallah 的意思接近為「若阿拉願意的話」。
本文中有提到奇慈飛遇到的警察對她說了這句話,而並未給予正面的答覆。這是阿拉伯語系國家的通用字,阿拉對他們(伊斯蘭教徒穆斯林)而言,就是唯一的真神,凡事都需經過祂的同意,這樣的宗教思維也影響了語言及生活。許多阿拉伯人習慣將這個詞掛在嘴邊,卻也導致了許多不確定性,就像奇慈飛遇到的狀況,根本無法確定到底下週去警察局能否拿到自己的居留證。
